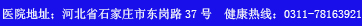记忆中的大暑,是古诗中老柳蜩螗噪,荒庭
2022/10/20 来源:不详曾几时何,最热衷于时令节气的,不是农耕文明的传承者,而是各个商家还有地产广告。如果上古先民知晓,他们用了无数辈总结、提炼、修正的经验,如今只是沦为广告创意的噱头和背景,不知作何感想,因为已经有了天气预报这个东西。
尽管,现代文明带来的对传统的冲击或毁灭,是不可避免而无可奈何的。但广告的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,到底还是让我们在行色匆匆的向前步伐中,猛然惊觉,原来古典诗词中的节气如此之美,甚至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大暑时节。
大暑,高温酷热,炎热之极,温热交蒸到达顶点,一年中的最热正在此时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如是说:
“大暑,六月中。暑,热也,就热之中分为大小,月初为小,月中为大,今则热气犹大也。”
古人为指导农事活动的而做的历法补充,以“五日为候,三候为气,六气为时,四时为岁”,因此一年的“24节气”共有七十二候,属于大暑的三候是:
“一候腐草为萤;二候土润溽暑;三候大雨时行。”
于是,大暑瞬间就变得可爱起来,日间听蝉鸣,夜里看流萤,就是付出点汗水,似乎也是值得的。更何况,城市里的盛夏,因有了这些,似乎就离钢筋水泥的冰冷就远了些,而多了些人间况味。
这种人情味的品咂,在宋代司马光的《六月十八日夜大暑》中别有趣味:
老柳蜩螗噪,荒庭熠耀流。人情正苦暑,物怎已惊秋。月下濯寒水,风前梳白头。如何夜半客,束带谒公侯。
创造了“司马光砸缸”典故的人,想来在生活中也是个妙人。这不,在当年的大暑之夜,他也许正慵懒地坐在家中清凉的某处,听老柳树上的知了声声地叫个不停,看空旷的庭院里萤火虫在漫漫飞舞,于是就开始感慨:当人还在为夏之酷暑而烦恼,世间万物早已洞悉了秋意。月光下,水面辉映着清冷的光,夜风中,且让它吹起披散的白发。
夏日如此美好,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,却在半夜来了紧急公文,于是诗人只好穿戴整齐接待来人。
读之,不禁令人“噗嗤”一笑,心声共鸣。美好的时光,总是不乏打扰者,所以且要珍惜。
关于大暑时节的萤火虫,唐末诗人徐夤的一首《萤》很是惊才绝艳,作为两朝进士、福建历史上的第二个状元,想来对于时势风向的把握也是敏锐的。
月坠西楼夜影空,透帘穿幕达房栊。流光堪在珠玑列,为火不生榆柳中。一一照通黄卷字,轻轻化出绿芜丛。欲知应候何时节,六月初迎大暑风。
无一字直点萤火虫,却句句写尽了流光飞舞的曼妙。当“月坠西楼”的夜晚升起,朦胧迷蒙中间,萤火虫开始出没于无声,穿过帘幕散落于房屋和庭院之中,带来了流光溢彩、堪如珠玉的莹润光泽。
于是这漫天荧光犹如点点星火,却又不是因为榆柳在燃烧,难怪会有车胤“囊萤夜读”的典故,给人以光明和希望,又像是画家笔触下的丹青泼墨,让时光变慢。于是,大暑的炎热因为萤火虫的曼妙姿态,而有了梦幻之色中的清凉之意。
萤火虫所带来的凉意,在杜牧的《秋夕》中更为身同感受:
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,坐看牵牛织女星。
虽然,诗词中的凉意扑面而来,但依然不能掩饰大暑“土润溽暑”的事实,“何以销烦暑”且看古人怎么说?
唐代的元稹是绝不会因为天气炎热而败下阵来的,一首《咏廿四气诗·大暑六月中》如是说:
大暑三秋近,林钟九夏移。桂轮开子夜,萤火照空时。瓜果邀儒客,菰蒲长墨池。绛纱浑卷上,经史待风吹。
莫以为大暑酷热就能阻挡了诗人对于生活的热爱,避开毒日头,等的就是夏夜,当月上中天,萤火虫也开始了舞蹈之时,夜宴才刚刚开始,瓜果、菰蒲、绛纱、经史……无一不是美好。
既然提到了瓜果,南宋宋人曾几也有诗《大暑》云:
赤日几时过,清风无处寻。经书聊枕籍,瓜李漫浮沉。兰若静复静,茅茨深又深。炎蒸乃如许,那更惜分阴。
想必,很多人都会对“经书聊枕籍,瓜李漫浮沉”心生向往,书中自有清凉意,而浸入水中的瓜李在浮沉中,似乎也带来了此消彼长、随波逐流的隐喻。
对于怎么度夏,白居易的《夏日闲放》就显得自我的多:
时暑不出门,亦无宾客至。静室深下帘,小庭新扫地。褰裳复岸帻,闲傲得自恣。朝景枕簟清,乘凉一觉睡。午餐何所有,鱼肉一两味。夏服亦无多,蕉纱三五事。资身既给足,长物徒烦费。若比箪瓢人,吾今太富贵。
不出门、不待客,睡竹席、穿简服,睡午觉、吃鱼肉……很有点自得自乐的味道,也颇为符合现代的极简生活方式。持同样生活态度的孟浩然,也有“散发乘夕凉,开轩卧闲敞。荷风送香气,竹露滴清响”的闲情逸致。
此外,黄庭坚“蕲竹能吟水底龙,玉人应在月明中。”《大暑水阁听晋卿家昭华吹笛》,尹志平的“一川禾黍正苍苍。了见西成有望……目前无事即仙乡。且恁随缘豁畅。”《西江月·时在天长正当大暑》,听笛、瞰景都是夏日心境。
不过,大暑的景致风物,除了标志性的萤火虫、荷花月色、竹风……还有“大雨时行”。
宋朝的范成大《大暑舟行含山道中,雨骤至,霆奔龙挂可骇》:
隤云暧前驱,连鼓讧後殿。駸駸失高丘,扰扰暗古县。白龙起幽蛰,黑雾佐神变。盆倾耳双聩,斗暗目四眩。帆重腹逾饱,橹润鸣更健。圆漪晕雨点,溅滴走波面。
这一段写暴雨的,仅“圆漪晕雨点,溅滴走波面”两句还颇有诗情画意,但这雨带来的后果也许是不堪设想的。千余年后,老舍的《骆驼祥子》中夏日暴雨的那个片段,何止是祥子悲剧一生的缩影,也是众生面对人生风雨的一段心理历程。
同样雨,落在不一样的时空,带来的雨思也有千千重。
唐人权德舆的“何朝逢暑雨,几夜泊鱼烟”《送从弟谒员外叔父回归义兴》,是羁旅的惆怅;
“半壁蕉云收暑雨,一帘絮雪扑晴风。”《初夏》是宋代王镃的应时欣喜;“流珠沾暑雨,改色淡朝烟。”《和黄充实榴花》又是宋代陈师道眼中的小细节……
面对大暑,也许,我们和古人一样,都在寻找“何以销烦暑”?
写出这一句心声的白居易以《销夏》应答:
何以销烦暑,端居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清风。热散由心静,凉生为室空。此时身自得,难更与人同。
我们比古人幸运的是,我们不仅有现代文明带来的冰箱空调电风扇,还有他们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销夏法——凉风生于诗词,诵读口角噙香。这是,我们的盛夏,也是我们的流年。